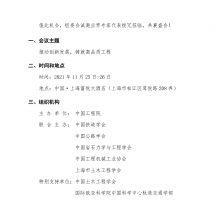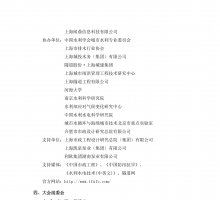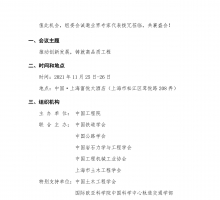保护主义的“民族”
|
在反对过度开发的斗争中,地标性建设是屏障还是利剑? 在美国的城市规划者中,20世纪60年代保护地标性建设法律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城市规划中真正鼓舞人心的时期:相关的社区、学者和建筑迷们都联合起来保护古建筑,使它们免受富有的开发商和强大的政治家的宏伟计划的伤害。并且,很明显的,大卫通常击败了巨人。但是,他们是否获得了过多的权利?越来越多的批判者认为这种保护已经变得不可收拾。包括左倾经济政策的书呆子、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 地标性建设在两方面受到攻击:建筑和经济。来自建筑类的批评家并不反对地标性标识,但是担心原本平淡无奇的建筑和社区会因为某些政治或感情原因而获得标志性。他们说,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公众只会欢迎建筑怀旧而不是创新。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认为,太多的地标性建设制约了新住宅和商业项目发展供应,从而限制了城市的经济潜力。结果就是,热门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过高。 在去年,哈佛经济学家埃德·葛兰泽在他的《凯旋城》中攻击了地标性,认为标志性建设所伴随的分区限制了密度或者增加了对停车场的需求。葛兰泽指向了由诺曼·福斯特为上曼哈顿东侧980麦迪逊大道设计的一栋30层的附加楼,这一设计被地标保护委员会否决了,尽管它会保持原有的1950年建造的石灰石画廊建筑。葛兰泽在其书中说:“限制发展的代价就是使被保护的区域变得更加昂贵和排他。”全国各地的城市政策博客们都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 对地标性建筑的审美批判也越来越多。去年春天,雷姆·库哈斯在纽约新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展览,对地标性建设进行了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报道说,“库哈斯有一幅画,画的是一群善意但是毫无头绪的保护主义者,他们对保护世界建筑遗产满怀热情,但是他们的工作最终却因为砍掉了历史中最困难的章节、为温驯的消费者创造了一副有品位的景色而受到贬低。” 这些问题在纽约可能最为突出。1963年,McKim、Mead and White(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被夷为平地,这至今仍让人隐隐作痛。但是类似争论已经在全国各地的老城市爆发了。《华盛顿城市报》称其为“保护主义的武装化”,包括Tenleytown历史协会极力阻止美国大学扩大校园面积,通过宣扬其地标地位,以保护相当平庸的1904年的神学院。 在波士顿,传统往往胜过新事物。建筑师和保护专家大卫·菲克斯雷说:“波士顿的南端对于你能对建筑所做的事的限制要求极为严格,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很好的理由。”人们不能对建筑做更改仅仅为了“保持事物原有的面貌。”有时官方会要求新建筑的设计要存在建筑的前后历史关系,即使该建筑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现代建筑。另一方面,在旧金山,有批评说由于对如1959年的北滩图书馆这类平凡的现代建筑的保护,现代主义正在被贬低。对此,古迹保护委员会已经给出了回应。 地标性建设的批评者和维护者趋向于在某一个关键点上达成一致:对地标性建筑的重要意义的质疑是由一个更大的问题所引起的——社会感到无力阻止那些无用的发展。莎拉·威廉姆斯,《新共和国》的建筑评论家说:“保护已经成为各种操作的一个全能工具。”“它正被用来阻止或决定发展的方向,因为城市规划者们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而不是因为这些建筑或地区在任何一个客观标准上是值得被保护的。” 然而,保护历史建筑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位于时代广场附近的纽约城市剧院的所有者曾试图把该建筑卖给开发商,他们想在该地建办公大厦。像葛兰泽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会为这样的市场效率鼓掌。但是纽约历史悠久的剧院是城市身份的一部分。当该城把剧院标志化后,它允许业主把开发权出售给相邻地块所有者。今天,时代广场有高大的办公楼,也有充满活力的剧院区。纽约历史区委员会的西麦·巴恩科夫说:“数千万美元涌入百老汇,它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主要经济引擎。”“它们仍在那里,因为它们是该城的重要标志。” 保护主义者认为中心城市的经济成功是因为地标性相关法律。葛兰泽和别人所无法理解的是,对于期望生活在曼哈顿或旧金山的这一庞大需求的存在,正是因为其建筑环境的建筑质量。
|
会员评论